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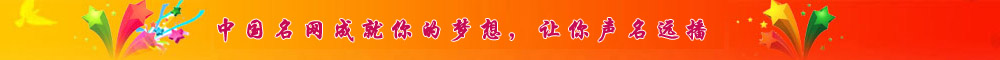
唐勇力:三唐画痴

唐勇力,著名人物画家,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协理事、中国工笔画学会副会长唐勇力教授。唐教授是中国当代具有代表性的工笔人物画家,兼长写意人物画。作品多次参展并获奖,出版有《唐勇力画集》、《唐勇力的画》等著作及画作多部。作品《敦煌之梦》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把人物工笔画得既有唐风而又非唐画,是著名还价唐勇力先生的一绝。因而,唐勇力被称为中国画坛反叛文人画的中坚。明清以降,文人画里论大行于世,重水墨,轻彩绘,尚写意,抑工谨的观念蔚然成风。长期浸淫于传统中的唐勇力,目光跨过数百年投向唐代,从其中寻找色彩与造型的全新气象,寻找健全的中国人物画画魂。打破工笔与意笔的传统对立,寻找现代工笔与意笔的另一个契合点,唐勇力为现代工笔人物画开辟出一个自由的创作空间。于是从《白居易诗意图》到《敦煌之梦》,你就可以看到“唐风”持续不断的发展脉络。
唐勇力:1951年出生,中国当代具有代表性的工笔画家,兼长写意画家,1985年考入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毕业后留系任教。曾任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人物画教研室主任,中国画系副主任、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硕士研究生导师、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99年12月调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任教,现为国画系副主任。作品曾参加第五、六、七、八、九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并多次获奖。出版有《唐勇力工笔人物画创作赏析》、《唐勇力的画》、《唐勇力客课稿》、《工笔人体艺术》、《唐勇力工笔人物画》、《世纪之交中国著名国画家—唐勇力》、《唐勇力工笔人物画的写意性》、《中国画家丛书—唐勇力》等十余种。
上世纪90年代,唐勇力在工笔人物画的创作上提出了“写意性工笔画”,多年来他一直坚持研究并实践这一课题。“当时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看到了中国传统画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越画越板刻,越画越僵死,大家都在用一种非常细腻的方法。”唐勇力说,“其实工笔的基本思想也是写意的,甚至比水墨画还要早,两者只不过技法不同,这种不同导致了工笔和写意的对立。”
身为具有代表性的工笔人物画家,唐勇力在回溯传统的同时对这一画种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作为画家,他很少将其思考宣这于口,但从他近年的画作中,我们或可以略窥一二。面对唐勇力的画作,我们可以明确地感到,尽管仿照了唐代人物画的造型与色彩,他的画与唐画之间还是存在着明显的不同。除去造型因素的一些顾然变动之外,这种差异感最主要是由于唐 勇力画中的那种被强调了的写意因素一这也正是他对传统工笔人物画所作的一项重要的改造。
传统的工笔人物画只能在轮廓线的内部平涂,渲染,但唐勇力却多彩取内外皆染的方法,轮廓线在许多地方被湮没在一片彩墨氤氲之中。人物与背景之间、人物与衣饰的各部分之间的边界由清晰变得朦胧起来。一切都被自然地融入如烟的神秘氛围之中。另外,唐勇力在人物面部及身体各部分的皴染中也适当地把握了虚、实关系。而在传统的工笔画中,一切都必须被严谨工整地刻画出来。对某些细节的虚化处理使整个画面摆脱了传统工笔画的那种工谨刻板的匠气,从而变得灵动起来。
事实上,长期以来笼罩在我们头脑中的意笔与工笔之分仅是手法与兴趣味的分野,从更深地层次上说,工笔与意笔一揉也在写“意”。只不过它们挥写时所依赖的程工不同罢了。顾恺之画裴楷时,在其颊上添了三毫,使得其形象“神明殊胜”,可谓中国古代人物画家追求和表现对象本身之内在意蕴的典范。在工笔与意笔的简单对立中,人们似乎全然忘记了这些动人的故事所蕴含着的深意,不但如此,在文人画理论的笼罩下,人们也往往忽视了一个画学史上的重要事实,即使最早的绘画理论大都是就人物画而提出的。正是从早期人物画的实践与品评中,古人才引发出了“意与象”、“形与神”等诸种对立。最初的写意,最高妙的写意存在于对“目送归鸿”的敏锐把握之中,只是在元代之后,“写意”才成为抒写出主观意兴和自由、粗率的代名词。无疑,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唐勇力的画才打破了工笔与意笔的传统对立模式,为现代工笔人物画开辟出一个异常自由的创作空间。
在中国上千年美术活动中,美术的一元和多元的时期都是短暂的。中国文人画是美术一元的产物,它的高度纯熟、完美,也伴随着封闭、保守,难以让人领略丰富、自由;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多元的时代,我们希望有什么样的美术风貌留于后世?仅我们一代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们的探索还未成熟、完美,但丰富性、多样性是能做到的。我们要以行动去创造多样性的艺术观念,多样性的风格流派,多样性的艺术语言。只要我们做工了,就会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痕迹。在进入新的世纪的时候,沉着的做法是少提口号,多做实事,平心静气去做画家该做的事,在一种自然关态下,让画家自由选择,积蓄力量,在数量和质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各派都有会有大家出现。只有这样,中国美术才能走向未来。
孔仲起取名,刘勃舒等名家题字,唐勇力的画室曰“三唐斋”。
我没有去过敦煌。
唐勇力去过5次。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十余年间他去了5次。还会有6次、7次吧?我同他相约,下次再去喊上我。
去和不去不一样,去一次和去两次不一样,一次有一次的收获。唐勇力的收获反映在两方面:有形的收获,即《敦煌之梦》系列作品,宗教佛缘,天上人间,在远古与现实的拉近中寻觅生命的走向和乐趣。有乐趣吗?那要看你以怎样的心态面对这段历史。是的,心态,那正是画家通过特殊的笔墨形式,在特定的时空、地域中力求表达的东西,或深沉驳杂,或轻松超脱。或神秘兮兮,或清丽可人,朗彻透明。而这一切,一定要你用心去体会,因为它镶嵌于敦煌那样的背景下。因为它独特、含蓄、朴拙,属于历史长河中潜藏已久的那部分淤积,金子在里边。谜底也在里边,作者痴痴傻傻地动了真情和犟脾气,一心要用画笔引领我们参观一处未曾见过的世界,于是有了《敦煌之梦》,也有了人们对画家用心的漠然和诘问:唐勇力在《敦煌之梦》中画了些什么?
就画家的人生设计而言,无形的收获可能更重要。在时间上发生于不惑之年,想法很多,富有激情。所谓激情,就是一个人面对人生命运的自我选择和激励。正是敦煌使唐勇力心头的追求明晰、坚定起来。一次次甘冒风沙朝觐去,一次次面壁自诘我在哪?拿起笔来画敦煌的同时,也即完成了他在美术之旅中的自我定位。敦煌与其内心需求相呼应,从而发生了早已是期待中、冥冥中的投身和归宿感。一副担子,别人望一眼走掉了,而他一望再望,认定这担子合该属于他、等着他,他深知这担子的重量。在莫高窟里、在这巨大的历史回音壁前他聆听嘱托,接受洗礼,坚定信念。唐勇力与中国画有铁定的死结,了解他的人决不会怀疑他的能力和作为。敦煌10年,确凿无疑地显示出这个人的独特、扎实及对国画艺术所表现出的信徒般的虔诚和投入。
单从作品看,《敦煌之梦》仅仅是画家笔下的一种题材、一个部分,与其他创作具有相对独立性。说它重要,因为从形式看,它是全新的、扎眼的,造型、色彩、笔法运用等基础因素皆饶有新意,不同凡响,全然不同于已有的国画样式。说它是工笔吗?是也不是,工笔中不乏写意性,以求传神及画面张力。说它是传统意义上的现代水墨?或者倒过来讲,是以现代水墨精神再现传统?似乎也不贴切。大创作需要大气魄,画家只管直奔主旨:画出一个全新的敦煌、一个为敦煌所浓缩了的文化现象和生存状态,以此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自身的认知。至于笔墨形式只是从属,一切服务于、服从于主题需要。
因为《敦煌之梦》,有了脱落法,使这批作品完全不同于以往绘画,亦有别于敦煌壁画而呈现一种全新的表现方法。美术史有可能疏于记载唐勇力的诸多名作力作,如《大唐遗韵》、《木兰诗》等等,“脱落法”和“虚染法”则足可使其驰名丹青,彪炳画苑。不独因其具备原创性和实用性,它更可佐证中国画在其历史演进的脚步,虽曾在今天散乱过,却没有停止。与巨大的社会进步相对应,以及面对从未有过的社会期望值,唐勇力这类人物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敦煌之梦》有其必然性。
《敦煌之梦》的又一重要性,是它的国画大观园中的匠心独具,别开生面。这都什么年代了?唐勇力画了些什么?谁爱看、有人买吗?有趣的是,这种小担心恰好对应着人们普遍抱有的大胆心,即市场经济对国画创作的负面影响,画什么、怎么样画不是源于艺术本身的感召,而是屈从于世俗低贱的挑剔,画家乐得轻松赚钱,又谁管艺术的灵魂暗自啼哭。艺术的灵魂维系于艺术家的良知。有什么样的良知便会有什么样的作为。唐勇力并非对敦煌一见钟情,而是在此找见了心仪中的图腾。只有借助敦煌这样的背景、载体,他之所学所悟、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他对西方绘画的了解和借鉴,他对东方美术的研习和阐发,以及东西方绘画相互沟通中属于他要找出的契合点等等,才能拼装在一个盘子里,经过其艺术加工,虔诚地捧给读者,这就是《敦煌之梦》。且不说它有多么高深,至少画家的创作态度极其认真,风格极其独特,以其形式和对作品内涵的深入挖掘,丰富了国画创作的多元化期待。
一点不错,你越是深入地阅读这些作品,就越是感受到其内在张力的冲击,就越是感叹唐勇力是何等不易!正是作品的巨大挑战性将会最终确定他对现代美术的杰出贡献。
《敦煌之梦》由“童年的记忆”、“人生”、“母亲”、“佛缘”、“岁月”、“梦悟”、“暮年”、“大漠人”等众多单元构成,每一幅作品均可独立成篇,而又有着内在联系,有机系统地反映着人生之旅的阶段性,及不同阶段的局限性、依赖性,尤其宗教依赖,贯穿始终,使人们的现实生活蒙上神秘色彩,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无一例外地被画家请进敦煌壁画,充当其中的一个角色,人即神、神即人。以佛教的观点,脱无明彀,戒烦恼河,人人皆可成佛。更何况,敦煌壁画亦来自于现实生活,耕种、收获、服饰、供养等,正是当年人们生活状态的再现。画家的聪明及非凡的悟性使他选择了嫁接,将现代人及壁画中的古人编织于一幅画面中,以工笔的细微刻划,保留脸部及手的肤色感、动感及现代感,其余部位,形体、服饰等,虽略有区别,在画面的总体构成上与古人融为一体,彼此依存,其结果是,画面在意象上有了多种解释,给读者以丰富的想象空间。一幅画的主角似也难以确定,孰为背景?谁在前台?读者可自行理解。
这样,唐勇力便把敦煌壁画画活了、引伸了。同时,人间现实生活也在其笔下披上理想化色彩,人对精神空间的追求哪怕是一场梦,也自有出处和根据。追求美好、向往美好,永远是人性中不泯的执著,如同画面中不时出现的佛光,它普照着远古,也辉映着当代。
脱落法与虚染法
前文已提及脱落法。
简言之,脱落法是将壁画中剥落的自然效果,经若干程序加工,刻意创作而形成一种全新的表现技法,产生独特的视觉效果。此法为唐勇力首创,这在国外出版的学术著作中已有记载,而国内画坛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纵观敦煌壁画,人们先是对人为毁损及千年风化剥蚀所造成的斑驳感惋惜不已,进而发现(尤其在专业人员眼中),这种剥蚀无疑是大自然对壁画的二次加工、再造,产生出新的艺术效果,赋予其新的历史承载量,使其更浑厚、更苍茫和更加耐人寻味。
那么,这种剥蚀可否借鉴、可否入画呢?唐勇力作了出有益而成功的尝试,这就是脱落法。
脱落法注重材料运用,采用绢及矿物色,通过厚涂及脱落,形成特有的肌理效果,意想不到的画面形式感,以此表达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审美倾向。作为一门技巧入画,须力戒糊乱涂抹,牵强附会,而要根据画面需求有序地展开,严格程序、把握规律。对此,画家在其教学中、著述中已有详尽讲解,笔者不多赘言。以笔者管窥,其工序之多、难度之大,非下大气力无以毕其功。
相比之下,由唐勇力率先提出的虚染法,对于传统工笔画具有更大挑战性和创新意义。
中国画在其发展演进中,经历代大师苦心经营而日趋完美。古老的画种如海绵一样,从不拒绝任何一滴水的融入,这才有百代繁盛,姹紫嫣红。历史上范宽的豆瓣皴、董源的披麻皴、倪瓒的轻墨法、近代黄宾虹的积墨法、张大千的泼彩法等,无不影响巨大,为画坛注入生机。唐勇力作为跨世纪的一代画家中的佼佼者,身处东西方文化大碰撞、大交流,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大动荡、大困惑,若能守住阵地已属不易,而要有所发明创造(并非臆造及各种异想天开的胡编乱造),在已臻完美的国画苑地再添新蕾,如同攀登巴那斯山(希腊神话中阿波罗和诗神缪斯的住所)一般,须有惊人的胆识和想象力。
传统工笔画要求细致入微,刻意求工,腰都累弯了,结果却是画面的刻板、匠气,千篇一律,很容易流入机械制作,重复敷色皴染完全可以找人替代,画家不动脑筋,作品少有灵气。虚染法用于工笔画创作,以意敷色、借色抒情,强调色彩的感情因素及自由发挥,打破传统桎梏,立足画面效果,简约、随意、浪漫,通过意趣的流动,带动色彩及画面整体效果的通灵、鲜活。其结果,机械简单的染色演变为创造性劳动,绘画过程不复枯燥,每天都会有新感觉、新发现。
虚染法由写意手法引伸而来。其与传统工笔画着色方法的显著区别是不受线的束缚,具体运用时可依据画面需要,有意识地将墨或色染至线条以外,墨色四周形成虚化,以此强化画面的透视感、滋润感,线实而色虚,相辅相成,浑然一体,形成空灵、飘逸的效果,既有传统意义上固守,又颇具现代审美情趣。
如同脱落法建立在对敦煌壁画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虚染法是特定生活空间和经历的赐予,只不过他以其过人的悟性发展了、放大了这种恩赐,经年累月的感悟化作艺术上的冲浪。人常说创新是中国画的灵魂。听话听音,分明传达着普遍担心其衰败、没落的潜台词。而唐勇力们的扛鼎、努力,足可打消这一顾虑。国画还年轻着,因为艺术家对生活的感受和捕捉总是簇新而异样。譬如唐勇力,正是江南水乡那山色空灵、雨雾濛濛所带给他的感受,引发了虚染法的最初萌孽。以虚染法绘制的工笔画与传统工笔画的一大区别,便是前者画面效果明显带有的朦胧感、滋润感,这正是江南水乡给予这位北方画家的精神愉悦,而他将其变成画面奉献给读者。
三唐斋主
除了唐勇力的个人素质以外,这里要特别强调造就一个绘画天才所特有的两大外力(当然,外因与内因总是密不可分)。
其一,唐勇力于1984年结业于中央美院国画系研修班之后,旋即考取中国美院国画系工笔人物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国画系人物教研室主任、国画系副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99年奉调中央美院,任中国画系副主任。南来北往,融汇贯通。两大美院,得其所长。其作品既有南方的轻灵秀丽,亦有北方之拙朴厚重。作品参加第五届、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美展,“百年中国画展”。出版《唐勇力画集》、《唐勇力课稿》等画册、工具书15种。
其二,唐勇力长期身处教学一线、科研一线,责任感、使命感同与生俱来的绘画热情在这一岗位上碰合,似乎天降大任,高扬好学精神。笔者拜读过其教学讲义汇编成的《古远回声》一书,不难看出他在教学中倾注的极大热情,他爱这个岗位。无论脱落法还是虚染法,他的任何一点发现、发明和心得,只要感到对学生有益,总是毫无保留地贯彻在教学中。讲解、演示的过程也即再次激发灵感的过程,课堂和宣纸对于他同样重要。理论研究与实践过程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如同阳光和水一样不可或缺,注定要成就这个人,留住他的画。
咦,唐勇力!
我在花家地中央美院新建大楼那宽敞的走廊里见到他时,他满面笑容,儒雅谦和,身材适中,略带自然卷的一头浓发使其显得年轻洒脱,更把由衷的谦和漾溢成学者儒雅,令人歆羡。我也在炎黄艺术馆、中国美术馆的展厅里碰到过他,直到坐在望京花园的画室里,我跟前的他一直是那副笑容、那种儒雅。
画室是画家的船,画笔是手中的桨,靠它们艺海荡舟。
尤其对于西湖边的那间画室,他内心充满情感,异常留恋。中国美院十五年,一间画室知冷暖,35岁至49岁这段最可宝贵的年华在此度过。宿舍———画室———饭堂,三点一线,天天如此。平平淡淡,毫无故事。接受采访时他曾说,怎么写呢?就写唐勇力是个画家,是个没有故事的人吧!
岁月匆匆,十年一瞬。最美好的感情总是愈久弥香。他说,也许到年龄了吧?时不时心里涌起一阵阵怀旧感。难忘那段时光、那间画室。
画室对面的楼层里住着留学生。隔窗相对,唐勇力的两个学生注意到老师的辛苦。杭州的盛夏,身上从早到晚都是汗津津的,连早晨冲凉,水都有温热感。尤其晚间,画室里异常闷热。学校放暑假,家家纳晚凉。人去楼空,惟有他那画室的窗户依旧亮着灯光。有一天夜间忽然响起敲门声,两个外籍学生站在门前,说,“唐老师,别人都回家了,大楼里就你一个人,天天窗户都亮着”。他们亲手做了绿豆汤,用个大搪瓷缸盛了,送与老师解暑。
他所以留恋那间画室,更由于学院特定的环境,教师队伍新老结合,学术氛围非常浓厚。孔仲起教授就很喜欢唐勇力的画风,关心他的创作,
到画室看望他说,“勇力你姓唐,唐人题材画得好,又是唐山人。我送你一个斋号,画室就叫‘三唐斋’吧。”
他曾与冯远毗邻,有四五年时间。冯住在他家楼下,曾话说这位邻居,不用看表,勇力的作息时间像钟表一样准确,每天六点半准进起床出门,白天家里再不见影,直到夜里12点,楼道里响起踢踏踢踏的上楼声,就知他回来了、门响了,十来分钟之后熄灯了、睡下了。一年到头,天天如此。除了一早一晚,其余时间全在工作室。
那时你欲找他,一般总在画室。他的一位学生毕业后分到外地工作,常来杭州,总到美院看望老师,每次来直奔唐勇力的工作室,一找一个准。有位学生来看他说,唐老师你知不知道外面有一个说法,有人给你起了个外号?
什么外号呀?
画痴!
“是吗?”唐勇力仍是那副儒雅的笑容。“这个外号挺好的。”
回首往事,他不无感慨地说,“我不是那种很聪明的人,不是靠顿悟,而是靠渐悟,慢慢体会。画家要有一点聪明,就我的情况看,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还是靠勤奋。”
“那时多好啊!”他说,没有电话(直到1994年,他的家里和画室才陆续安上电话),没有现在这么多事。没有房子、工资、待遇等诸多干扰,对于这些事脑子里一片空白。画画和围绕画画展开的研究几乎是生活中的一切。工资够吃饭就满足了,发了工资换一把饭票,每天到食堂打饭吃,吃罢饭往画室一钻,日子就这么过着。也不买衣服,夏天有件背心,冬天冻不着就行,感觉很舒服。
尤其下雨天,感觉最美好。杭州多雨,唐勇力特别喜欢下雨天,与他细腻的性格有关吧?也可能杭州的雨水、气候和经历细化了他如今这般性格,进而影响其画风,古装仕女系列那亦真亦幻的人物布置,花山树影,亭台阁榭,多取材于西湖给予他的感受。
下雨了,也画累了。雨水落地、敲打树叶的欢快声,激起他孩子般的喜悦,到底将其拽出画室,放松一下,骑自行车绕西湖岸边转一圈,是为特有的一种采风、一种享受。行人极少,偶有一两对情侣携手,湖水里一两只小船荡动,生动有致,美妙极了!苏堤白堤,两岸垂柳。雨打夹竹桃,水溅湖心亭,把人看得痴痴迷迷的,不知身在何处。
匆匆忙忙,弹指一挥。十数年如一日,很快就过去了。生活总是一段段地走。未曾想到有一天还会告别中国美院那间约有13平方米的工作室。离开杭州前夕,内心多少留恋!这么美的地方、这么长的时间,很多景点只是听说,从未游览过。说走就要走了,怅然若失,说不出的留恋。若不是行期已定,再逗留几天多好!生活就是这样,一旦错过才知其美好,一旦失去,再难以找回,而只把美好的记忆留在心中。好在,作为画家,这些记忆总会在笔端有所流露。
那是个夜晚,他打的到火车站。一路上透过车窗眺望,灯光灼灼,树荫闪过。从此要离开这儿了。因为奋斗过,所以挚爱;因为成就过我,所以恋恋不舍。不知不觉中,竟有些泪眼模糊。
一晃又4年。在感情上,杭州仍是他的驿站,难以割舍。也仍是他的梦,牵着挂着。又有敦煌。又有脱落法、虚染法。所以呀,要想做一位好画家、名画家,也真够累的。
最新相关文章
文章点击排行